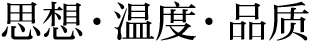从29到27:烈士影像入框 英魂终有模样
延庆报
2025-08-19 17:24

004
 八路军挺进平北
八路军挺进平北 烈士墙上终于“挂”上了祁式超的照片
烈士墙上终于“挂”上了祁式超的照片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内,44块烈士生平展板如沉默的丰碑矗立。其中29个肖像位置的空白轮廓,是岁月留下的未愈伤疤,无声叩问着历史:那些消逝于烽火的面容能否重现?那些被战火割裂的故事能否接续?这不仅关乎个体生命的完整叙事,更牵动着民族记忆的根基。
悬像待英魂
29位烈士的“未完成”叙事
 王永和烈士
王永和烈士在众多名字中,王永和烈士尤为令人记忆深刻。这位原名王海清的延庆大庄科乡香屯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昌延联合县三区、十三区区长;由他担任队长的滦昌怀顺联合县武工队,更在烽火岁月中留下了一段段传奇故事。这支队伍起初仅有十几人、枪支不足十支,却个个精干、能力出众——既擅长对伪军开展策反工作,又能紧密联系群众、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两次奇袭昌平城的壮举:首战极大鼓舞了士气,再战则迫使敌人回兵守城,不仅粉碎了“扫荡”计划,更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部分日军撤离后,伪满洲军进驻北苑机场。为保卫和巩固抗日胜利果实、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平北地委与昌顺县委决定在平原地区扩充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扩军运动,却不料遭到敌人阻击。9月22日,500余名伪满洲军将奶子庙村团团包围,随即进村大肆搜捕,见可疑人员便抓,王永和不幸落入敌手。
随后,伪满洲军将全村人驱至村南娘娘庙前的空场,王永和等人被一同押到此处。伪军头目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宣传,污蔑王永和所谓“罪行”。面对这般污蔑,愤怒的王永和面向数百名伪军及围观群众高声疾呼:“我们受苦人参加革命,是为了报仇雪恨,是为了翻身求解放!真正有罪的,是那些欺压百姓、剥削人民的家伙!我投身革命已近八年,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痴心妄想!”敌人被这番话激怒,当即对王永和等3位同志下了毒手。随着一阵罪恶的枪声,3位烈士倒在了血泊之中,王永和年仅3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1983年6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追认王永和为革命烈士。
今年4月,延庆区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起倡议,为包括王永和在内的29位有姓名、有事迹却无影像留存的烈士寻访照片线索,盼社会各界助力,让英雄真容为世人所识。倡议一经发出便得到热烈响应,一位知情人士一次性提供了3位烈士的相关线索,王永和的影像线索正是其中之一,经纪念馆与家属细致沟通核实,王永和烈士的照片率先得到确认。如今,这张照片的入藏,让英雄的形象从文字记载的抽象轮廓,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具象记忆,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凝视与缅怀中得以永续传递。
破界连史脉
区域协作解开家族八十余年心结
而令人更为惊喜的线索出现在7月。在京津冀“为胜利吹响号角”——第二届红色文化研讨会上,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吴晨晨在分享中,提及了一位有姓名、有故事、无影像资料的名为祁式超的烈士,简单的分享,让原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烈士纪念园主任王志忠想起了一段往事。散会后,他主动添加吴晨晨的微信,分享了关于祁式超烈士的关键线索,这些线索则引出了一段跨越八十多年的家族牵挂。
祁式超出身于山西的一个富裕大家族,因战乱随家人迁居至江苏。聪明好学的他,早早对革命有了深刻的理解。因目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家国沦丧的切肤之痛让他十几岁便毅然告别家人,踏上了革命道路。他曾就读于华北联大音乐系,将知识与理想融入烽火征途,1938年加入八路军后,辗转多地投身抗日洪流。在平西挺进军挺进剧社担任音乐教员时,他教战士们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曾在山谷间激荡,成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到平北后,他在宣传科任干事,延庆的山山水水间,曾回荡着他唤醒民众斗志的歌声,而他却在残酷的战争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家人虽在后来收到过部队寄来的烈士证,知晓他已牺牲,却始终不清楚他安葬何处。老母亲临终前,攥着祁式超妹妹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你‘三哥’的安葬地,弄清楚他最后留在了哪里,把他带回来。”这份沉甸甸的嘱托代代传递,多年来,祁式超的外甥仲星跑遍天津、河北等地,逢人便打听“祁式超”的名字,终于辗转找到了赤城县——这里,可能有着舅舅最后的踪迹。接待仲星的,正是王志忠。这位深耕烈士纪念工作多年的老主任,为他细致梳理了祁式超牺牲的壮烈经过:1943年秋,伤病缠身、近乎失明的他在赤城黑龙潭大海陀病休所遭日寇搜捕。面对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凭一腔血性抱住敌人厮打,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最后因寡不敌众,与6名战友一起被敌人乱刀砍杀,血肉模糊,身首异处,壮烈牺牲。
同时,王志忠还向仲星讲述了祁式超烈士安葬的来龙去脉:祁式超烈士最初安葬在黑龙潭,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赤城县修建烈士公墓,祁式超与其他烈士的遗骨被集中迁葬至雕鹗烈士纪念园,与众多无名烈士合葬一处。园内,与祁式超合葬的80余位烈士,多是牺牲在赤城的异乡英烈。不同于本地烈士多已迁回原籍、有了明确归属,这些异乡英魂因身份未详,始终长眠于此,成为纪念园里沉默的守护者。八十余载光阴流转,烈士遗骨早已与泥土相融,又因当年是集中合葬,终究难再分辨——想单独寻出祁式超的遗骨,已是奢望。仲星曾想去舅舅牺牲的黑龙潭看看,可当年那场战斗的发生地,如今已是军事管理区,终究没能踏入。最终,他在雕鹗烈士纪念园捧回一抔黄土——这浸润着山河记忆的黄土,成了他与舅舅跨越八十余载的特殊重逢。也是在这次寻亲过程中,王志忠得到了一张祁式超参加革命前的童年旧照——这是他唯一留存的珍贵影像。就此,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展板上的空白轮廓数量暂时定格在了27处。
 祁式超烈士
祁式超烈士 “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参会代表到八达岭烈士陵园祭奠英烈
“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参会代表到八达岭烈士陵园祭奠英烈 协理固根基
“三位一体”机制重塑历史脉络
平北地区的抗战历史,原是由延庆、密云、昌平、怀柔、赤城、怀来等地共同勾勒的血脉长卷,其烽火岁月始终与“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抗战方针紧密交织。正是这一战略指引,让平北成为链接冀东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桥梁,更让各地的战斗故事天然具备血脉相融的历史关联。然而,地域行政划分的阻隔,叠加各地史料保存方式与条件的差异,使得祁式超、王永和等众多烈士的事迹长期处于“分置”状态:延庆的档案中,或许留存着某位烈士战斗的具体足迹与工作细节;赤城或密云的卷宗里,可能记载着同一位烈士牺牲的悲壮场景与安葬脉络。遗憾的是,这些散落各处的珍贵史料碎片,因长期缺乏系统化的跨区域串联机制,协同梳理力度薄弱;加之平北多山多林、曾交通闭塞,战争年代的史料多靠口耳相传,或仅以家书、证明、笔记等零散纸质形式留存,缺少统一规范的整理归档——这直接导致部分烈士的生平轨迹在行政区划边界处出现令人痛心的断裂,英雄的人生拼图也因此长期留存着难补的空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24年,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牵头举办的首届“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其深远意义愈发凸显。它不仅如一座精心架设的桥梁,有力打通了横亘已久的地域壁垒,更构建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的协作框架: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对接平台、制定跨区域的史料共享规范、协调各地档案部门深度参与,让官方档案、地方记载、口述历史乃至家族珍藏的影像与故事,得以在权威主导下实现高效汇集、精准比对与深度整合。而将平北抗战史料上线“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更让地方记忆融入全国性抗战史料体系,为跨区域协作拓展了更广阔的辐射维度。
祁式超烈士信息的重大突破,正是这一机制高效运转的生动注脚:吴晨晨在研讨会上的讲述,是向平北抗战研究网络发出的“寻人启事”;台下王志忠的即时响应与线索提供,是区域内历史记忆的深度共享;祁式超外甥仲星跨越八十余年的家族寻根,是家属私人记忆与官方历史的珍贵交汇;最终,一张尘封的童年照片重见天日,填补了英雄影像的空白。
这一系列环节的紧密衔接与高效互动,精准印证了“三位一体”机制的运作逻辑,让参与者深切体会到:要整合平北抗战历史的壮阔全貌,让每位英雄的人生轨迹清晰完整地呈现在后人面前,让历史根基筑得更牢更实,必须依靠持续纵深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区域协作与史料共享机制。这场研讨会不仅是年度性的交流场合,更是弥合历史鸿沟、接续英雄史脉、凝聚各方力量的创新实践平台,是践行“为英雄补全人生 为历史筑牢根基”这一崇高使命不可或缺的实践支撑。
如今,展厅里的27个空白轮廓仍在静静等候。或许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页斑驳的家书,便能让另一段断裂的历史重归完整。为烈士寻亲,是历史交付的必答题,这条镌刻着初心与敬意的寻亲之路、归乡之途,在社会各界与万千民众的共同接力下,我们必将陪着英魂坚定走下去——直到每一道空白都被鲜活的生命事温暖填满。
 吴晨晨在“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上讲述平北烈士的故事
吴晨晨在“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上讲述平北烈士的故事 “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参会代表参观大庄科红色平北第一村纪念馆
“三位一体”红色文化研讨会参会代表参观大庄科红色平北第一村纪念馆


打开APP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