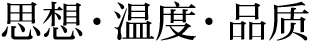孟姜女文化的北京特色(一)
延庆报
2025-07-18 11:02

003
延庆是中国修筑长城较早的地区,在战国燕昭王时期即有长城修建。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延庆为燕国上谷郡的中心地区,因此修建长城的历史达2300多年,孟姜女传说自然在延庆地区广泛流传,是北京地区孟姜女传说的主要流传区。自明代以来,延庆人民就以传统孟姜女故事为基础,结合地方风物、节俗等创编出一系列孟姜女故事,迥然有别于中国其它地区,作为北京长城文化的代表,口口相传直到现在。
国家级非遗项目“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池尚明,曾经搜集整理《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长城》,讲述了孟姜女的前生,这在中国来说独一无二,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兰香姑娘十分贤惠,她伺候丈夫,孝顺公婆,人们赞不绝口。后来,婆婆突然病倒,对兰香说:“要治好我的病,得到北方去采一种神药。”兰香在院中摆下天地桌,烧了三炷香,跪下磕仨头,两眼泪汪汪地说:“万事天为上,兰香真心救婆婆。我若是诚心诚意,爬山过河别让我受伤;我若是假心假意,让我一命见阎王。”然后兰香独自出发寻找神药。一天傍晚,她遇到三个恶人扑来,兰香拼命奔跑,三人在后面紧追。
兰香跑上山头,站在一块大白石头上,前方就是万丈深渊。她想:“要想不被抓住,只有跳崖!”死,她不怕,但没有找到神药,让她十分伤心。这时,白石头说话了:“好姑娘,莫悲伤,有什么困难我来帮!”
兰香低头一看,脚下的白石头变成白马,自己正骑在马背上。三人离兰香很近了,她举起手里的木棍儿,用力朝马尾巴打去。那匹马腾空而起,驮着兰香飞走了。马尾巴被打落在山头,变成一堵石墙,挡住三个人。
这段石墙,就是最早的一段长城。
兰香骑着白马睡着了,梦里白马说:“不打掉尾巴,我飞不起来,现在飞起来了,可是血要流完了。”兰香惊醒,忙摸马尾:“全是血,怎么办?”白马说:“兰香,你是好姑娘,真心实意救婆婆。现在,你婆婆的病已经好了!”兰香十分喜悦。白马说:“兰香,我飞不动了,就要落下去变成石头,可你怎么办?我救了你,现在岂不是又害了你?”兰香说:“既然婆婆病好了,我的心愿得以实现,我愿和你一同去,永远不分开!”白马和兰香坠落下来,白马变成岩石,兰香变成葫芦籽。
传说,凡是修长城的地方,都是白马的血滴落的地方。长城有多远,白马就驮着兰香飞了多远。一百年后,兰香变成的葫芦籽,被喜鹊叼到孟家窗台上。孟老汉看到后,把葫芦籽种下,葫芦长大后,里面竟有个小女孩,她就是孟姜女,转世投胎的兰香。
这个流传在延庆地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兰香,她是孟姜女的前生。
孟姜女是民间百姓的虚构人物,但其背后也有历史原型,研究者们捋顺出一个大致认可的脉络:
其发端于《左传》所记,发生在春秋时期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的一场战事:“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斗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在文中,杞殖即杞梁、华还即华周。
在这场战事中,齐侯自己受伤,却依然约战。杞梁和华周受命,连夜布防在莒国郊外。没有想到,他们最先遇到了莒国国君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但两国相比,莒国比齐国实力差很多,从“齐侯”与“莒子”的爵位就可以衡量出来。西周时期,周天子通过实行宗法制与分封制,建立起等级严密的宗法社会,周天子为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王下分封诸侯,各诸侯国则通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区别出国君等级,莒国国君比齐国国君低了两个等级。
杞梁被擒,大概也仰仗齐国的强大,采取傲人的态度惹恼了莒子,因此被杀。但杞梁刚死,莒国和齐国便讲和了。齐侯回来的时候,在郊外遇到杞梁妻迎接丈夫的尸体,齐侯派使者去吊唁。杞梁妻回绝:“他如果有罪过,难道不是有辱使命吗?不值得吊唁!如果他没有罪过,就应该按照礼制在祖屋为其设置灵堂后再吊唁,我不接受在郊外进行吊唁的做法!”齐侯感到杞梁对国有功,便到其家举行祭奠仪式。通过杞梁妻的言辞可以看出,她深谙周代礼制,是个恪守礼法、冷静理智、处乱不惊的贵妇。
这个历史事件在古代颇有影响,因此中国很多古籍都曾引用过,但在引用时内容有所增减,词语有所变化。《礼记·檀弓》:“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增加哭的情节。《孟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因哭改变国俗,可见其影响巨大。汉代刘向《说苑》:“杞梁、华周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陀,而隅为之崩。”增加了杀敌战果,因哭城崩的情节。汉代刘向《列女传·齐杞梁妻》:“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諴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此之谓也。颂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增加了杞梁妻的复杂心理活动及世人对杞梁妻的高度好评,营造出杞梁妻上无父母呵护、中无丈夫守护、下无子女奉养,孤苦伶仃的悲惨境遇,因此万分绝望投水而死。
清代陈梦雷《明伦汇编·闺媛典》把各种资料比对后提出疑问:“夫既有先人之敝庐,何至枕尸城下。且庄公既能遣吊,岂至暴骨沟中。崩城之云,未足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长城,长城筑于威王之时,去庄公百有余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始皇所筑之长城也。”综上所述,《左传》所记确有其事,而后世古籍再言杞梁,都融入了作者的改编。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是以春秋战国为背景,第六十四回《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以《左传》的杞梁事为核心,再进行小说体艺术创作,使得杞梁人物更加丰满,杞梁妻的性格更加鲜明。杞梁忠勇重义,面对莒军围困,他与战友孤车奋战,拒绝莒国招降,始终以完成君命为信念。他重诺守节,初因“二人共一乘”深感耻辱,但在其母教导后毅然赴险、英勇无畏,单车突阵时能杀伤莒军过半,最后以重伤殉国展现出非凡的勇武。孟姜则庄重守礼,面对齐庄公于郊外吊唁的失礼之举,她明确拒绝,体现对礼法的重视与尊严的维护。她对杞梁用情至深,杞梁死后其极度悲痛,展现出对丈夫的深情挚爱与无尽哀思,甚至作为妇女的榜样改变国俗。
西晋崔豹《古今注·音乐》:“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在古代,杞梁妻的事迹在民间被广泛传唱,并收入官方乐府。如明代郭勋《雍熙乐府》当中的《端正好·集杂剧名咏情》有句:“我待学孟姜女般真诚性,我则怕啼哭倒了长城。”《点绛唇·团圆梦》有句:“孟姜女长哀恸,倾彼城隅。”《粉蝶儿·思情》有句:“今宵独宿牙床,闷的我似孟姜女,泪汪汪止望清明到,谁想过重阳,空藏下寄来书添望想。”《新水令·王魁负桂英》有句:“有情的长城下做夫妻,范杞郎一身亏收江南,待学那孟姜女千里送寒衣,怕俺那谢天香,化做一块望夫石。”清代王奕清《御定曲谱》有《正宫近词·划锹令》:咱每本是簪缨裔,官差来此苦寒地,儒身挂荷衣,勉随队里,河堤运泥,筑城万里,大家努力。”民国年间不着编人《平剧戏目汇考》,详细记录《孟姜女戏》的故事情节,但把“范喜良”记作“范纪良”。其中:“孟父另遣家童兴儿及小婢春环伴送同行,中途兴儿忽起不良之心,将春环杀死,欲求欢于孟姜,孟姜计诱入山洼,蓦然推其而下,于是只身登程。”“时蒙恬为监督大臣,见孟姜美色,献于始皇。”“孟姜乃至望萍桥上,遥拜父母,竟投海而死。”等情节另有格调。
西晋左思之妹左九嫔,名芬,字兰芝。泰始八年(272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修仪,位比关内侯,后为贵嫔。左芬是中国较早的女文学家,她很有才名,司马炎出于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将其纳入后宫。《晋书》记载的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所以根本得不到皇帝的宠幸,左芬作《杞梁妻赞》以自喻:
遭命不改,逢时险屯。夫卒莒埸,郊吊不宾。
哀崩高城,诉情穹旻。遂赴淄川,托躯清津。
唐代,杞梁妻的故事从“哭都城”演变为“哭长城”,杞梁妻从无名演变为“孟仲姿”,“杞梁”演变为“杞良”,完成孟姜女故事的基本雏形。故事主题则通过控诉秦始皇修长城的暴政,反映苦役筑长城的悲剧。唐代敦煌残卷《同贤记》载:“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何因在此?’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逃役筑长城,不堪辛苦,逃匿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妻。’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夫妇礼毕,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并筑城内。超不知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哭,向城号叫。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杞良。即抛骨取之,多是其骨。仲姿不辞归家,乃穿其骨,衣之以衣,裹之以棺,哭而葬之。”唐代首次出现了“仲姿”之名,后世演变为“孟姜女”。
在《同贤记》中,杞良自述为燕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北京产生了关系。在古代燕地虽大,但北京历来为其核心区域。可以推测,孟姜女所居亦为燕地,杞良所筑之长城亦为燕地长城,这就大概和延庆产生勾连。孟家是当地大户,知道秦廷有用钱赎役,或者以家仆代替服役的制度。因此夫妇礼毕,孟超就给杞良定策,让其自往长城工地,然后再派仆人将其替换回来,夫妻即可安稳度日。出人意外的是,杞良刚返回工地,就被主管劳役的官员打死。仆人到工地代替杞良,杞良的尸体已被筑进长城,立刻返回禀告。仲姿得知消息,便到长城工地哭夫,致使长城崩倒,露出的白骨错杂,一时分不出哪些尸骨是杞良的。孟姜女于是挑挑捡捡,把杞良散乱的白骨拼凑成人形,固定之后给尸骨穿上衣服,装进棺材后哭着将其埋葬。
唐代佚名《琱玉集》中的《感应篇》出自《同贤记》,把辨认尸骨的情节进行了细化,使其融入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便将归葬之也。”“滴血认亲”是中国古代的发明,扎根历史将近两千年,孟姜女采用的是“滴骨法”。三国时期,吴国谢承《会稽先贤传》:“(陈)业兄渡海,复见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十六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沥骨上,应时欿血,余皆流去。”由此,“滴骨验亲”之法被奉为圭臬。唐代李延寿《南史》记载,孙法宗之父死于大海,他操刀沿海岸寻找,见到枯骨就用“滴骨法”,十余年后,他体无完肤,仍没有找到。
清代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湖上笠翁曰:余读他传,有谓秦孟姜,富人女也,赘范杞梁,三日,夫赴长城之役,久而不归,为制寒衣。送之至长城,寻问,知夫已故,乃号天顿足,哭声震地,城崩,寻夫骸难认,啮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为夫骸,负之而归,至潼关,筋力已竭,知不能归。乃置骸岩下,坐其傍而死。潼关人重其节义,立像祀之。”可见,在清代时期,“滴血认亲”已经是孟姜女故事的重要情节。延庆地区的孟姜女故事,即沿袭“滴骨法”认亲的情节。
在唐代敦煌石窟发现一首小曲:“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骆山下雪纷飞,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归还。”增加了送寒衣的情节,与《感应篇》虽同为唐代,但情节也有创新。明清时期,孟姜女的故事被进一步加工,有了“燕子送葫芦籽”“葫芦生女”等情节。
元明清时期,孟姜女故事融入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情节则更加丰富多彩。如《理学汇编·文学典》词曲部汇考有曲目《孟姜女》、明代解缙《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戏,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在元杂剧《孟姜女送寒衣》当中,孟姜女哭倒长城后,和想要强娶的秦始皇斗智周旋,十分接近现代人所熟知的情节。其后,从清代至今流传的各种大剧种、小地方戏、电影、话本等,大都以此为蓝本进行创作,“杞梁”谐音为“喜良”,被冠以“范”或“万”姓,但在具体情节上各有特色。因地区不同,民间所塑造的孟姜女形象也不同。北方地区的孟姜女大都悲壮,符合北方人的性格特征。南方地区的孟姜女大都细腻,有时加入奇幻色彩。都融入各地的地方风物,把孟姜女元素附加于山、水、墓、石等,成为地方的特色文化。(未完待续)
国家级非遗项目“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池尚明,曾经搜集整理《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长城》,讲述了孟姜女的前生,这在中国来说独一无二,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兰香姑娘十分贤惠,她伺候丈夫,孝顺公婆,人们赞不绝口。后来,婆婆突然病倒,对兰香说:“要治好我的病,得到北方去采一种神药。”兰香在院中摆下天地桌,烧了三炷香,跪下磕仨头,两眼泪汪汪地说:“万事天为上,兰香真心救婆婆。我若是诚心诚意,爬山过河别让我受伤;我若是假心假意,让我一命见阎王。”然后兰香独自出发寻找神药。一天傍晚,她遇到三个恶人扑来,兰香拼命奔跑,三人在后面紧追。
兰香跑上山头,站在一块大白石头上,前方就是万丈深渊。她想:“要想不被抓住,只有跳崖!”死,她不怕,但没有找到神药,让她十分伤心。这时,白石头说话了:“好姑娘,莫悲伤,有什么困难我来帮!”
兰香低头一看,脚下的白石头变成白马,自己正骑在马背上。三人离兰香很近了,她举起手里的木棍儿,用力朝马尾巴打去。那匹马腾空而起,驮着兰香飞走了。马尾巴被打落在山头,变成一堵石墙,挡住三个人。
这段石墙,就是最早的一段长城。
兰香骑着白马睡着了,梦里白马说:“不打掉尾巴,我飞不起来,现在飞起来了,可是血要流完了。”兰香惊醒,忙摸马尾:“全是血,怎么办?”白马说:“兰香,你是好姑娘,真心实意救婆婆。现在,你婆婆的病已经好了!”兰香十分喜悦。白马说:“兰香,我飞不动了,就要落下去变成石头,可你怎么办?我救了你,现在岂不是又害了你?”兰香说:“既然婆婆病好了,我的心愿得以实现,我愿和你一同去,永远不分开!”白马和兰香坠落下来,白马变成岩石,兰香变成葫芦籽。
传说,凡是修长城的地方,都是白马的血滴落的地方。长城有多远,白马就驮着兰香飞了多远。一百年后,兰香变成的葫芦籽,被喜鹊叼到孟家窗台上。孟老汉看到后,把葫芦籽种下,葫芦长大后,里面竟有个小女孩,她就是孟姜女,转世投胎的兰香。
这个流传在延庆地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兰香,她是孟姜女的前生。
孟姜女是民间百姓的虚构人物,但其背后也有历史原型,研究者们捋顺出一个大致认可的脉络:
其发端于《左传》所记,发生在春秋时期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的一场战事:“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斗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在文中,杞殖即杞梁、华还即华周。
在这场战事中,齐侯自己受伤,却依然约战。杞梁和华周受命,连夜布防在莒国郊外。没有想到,他们最先遇到了莒国国君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但两国相比,莒国比齐国实力差很多,从“齐侯”与“莒子”的爵位就可以衡量出来。西周时期,周天子通过实行宗法制与分封制,建立起等级严密的宗法社会,周天子为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王下分封诸侯,各诸侯国则通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区别出国君等级,莒国国君比齐国国君低了两个等级。
杞梁被擒,大概也仰仗齐国的强大,采取傲人的态度惹恼了莒子,因此被杀。但杞梁刚死,莒国和齐国便讲和了。齐侯回来的时候,在郊外遇到杞梁妻迎接丈夫的尸体,齐侯派使者去吊唁。杞梁妻回绝:“他如果有罪过,难道不是有辱使命吗?不值得吊唁!如果他没有罪过,就应该按照礼制在祖屋为其设置灵堂后再吊唁,我不接受在郊外进行吊唁的做法!”齐侯感到杞梁对国有功,便到其家举行祭奠仪式。通过杞梁妻的言辞可以看出,她深谙周代礼制,是个恪守礼法、冷静理智、处乱不惊的贵妇。
这个历史事件在古代颇有影响,因此中国很多古籍都曾引用过,但在引用时内容有所增减,词语有所变化。《礼记·檀弓》:“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增加哭的情节。《孟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因哭改变国俗,可见其影响巨大。汉代刘向《说苑》:“杞梁、华周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陀,而隅为之崩。”增加了杀敌战果,因哭城崩的情节。汉代刘向《列女传·齐杞梁妻》:“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諴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此之谓也。颂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增加了杞梁妻的复杂心理活动及世人对杞梁妻的高度好评,营造出杞梁妻上无父母呵护、中无丈夫守护、下无子女奉养,孤苦伶仃的悲惨境遇,因此万分绝望投水而死。
清代陈梦雷《明伦汇编·闺媛典》把各种资料比对后提出疑问:“夫既有先人之敝庐,何至枕尸城下。且庄公既能遣吊,岂至暴骨沟中。崩城之云,未足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长城,长城筑于威王之时,去庄公百有余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始皇所筑之长城也。”综上所述,《左传》所记确有其事,而后世古籍再言杞梁,都融入了作者的改编。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是以春秋战国为背景,第六十四回《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以《左传》的杞梁事为核心,再进行小说体艺术创作,使得杞梁人物更加丰满,杞梁妻的性格更加鲜明。杞梁忠勇重义,面对莒军围困,他与战友孤车奋战,拒绝莒国招降,始终以完成君命为信念。他重诺守节,初因“二人共一乘”深感耻辱,但在其母教导后毅然赴险、英勇无畏,单车突阵时能杀伤莒军过半,最后以重伤殉国展现出非凡的勇武。孟姜则庄重守礼,面对齐庄公于郊外吊唁的失礼之举,她明确拒绝,体现对礼法的重视与尊严的维护。她对杞梁用情至深,杞梁死后其极度悲痛,展现出对丈夫的深情挚爱与无尽哀思,甚至作为妇女的榜样改变国俗。
西晋崔豹《古今注·音乐》:“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在古代,杞梁妻的事迹在民间被广泛传唱,并收入官方乐府。如明代郭勋《雍熙乐府》当中的《端正好·集杂剧名咏情》有句:“我待学孟姜女般真诚性,我则怕啼哭倒了长城。”《点绛唇·团圆梦》有句:“孟姜女长哀恸,倾彼城隅。”《粉蝶儿·思情》有句:“今宵独宿牙床,闷的我似孟姜女,泪汪汪止望清明到,谁想过重阳,空藏下寄来书添望想。”《新水令·王魁负桂英》有句:“有情的长城下做夫妻,范杞郎一身亏收江南,待学那孟姜女千里送寒衣,怕俺那谢天香,化做一块望夫石。”清代王奕清《御定曲谱》有《正宫近词·划锹令》:咱每本是簪缨裔,官差来此苦寒地,儒身挂荷衣,勉随队里,河堤运泥,筑城万里,大家努力。”民国年间不着编人《平剧戏目汇考》,详细记录《孟姜女戏》的故事情节,但把“范喜良”记作“范纪良”。其中:“孟父另遣家童兴儿及小婢春环伴送同行,中途兴儿忽起不良之心,将春环杀死,欲求欢于孟姜,孟姜计诱入山洼,蓦然推其而下,于是只身登程。”“时蒙恬为监督大臣,见孟姜美色,献于始皇。”“孟姜乃至望萍桥上,遥拜父母,竟投海而死。”等情节另有格调。
西晋左思之妹左九嫔,名芬,字兰芝。泰始八年(272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修仪,位比关内侯,后为贵嫔。左芬是中国较早的女文学家,她很有才名,司马炎出于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将其纳入后宫。《晋书》记载的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所以根本得不到皇帝的宠幸,左芬作《杞梁妻赞》以自喻:
遭命不改,逢时险屯。夫卒莒埸,郊吊不宾。
哀崩高城,诉情穹旻。遂赴淄川,托躯清津。
唐代,杞梁妻的故事从“哭都城”演变为“哭长城”,杞梁妻从无名演变为“孟仲姿”,“杞梁”演变为“杞良”,完成孟姜女故事的基本雏形。故事主题则通过控诉秦始皇修长城的暴政,反映苦役筑长城的悲剧。唐代敦煌残卷《同贤记》载:“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何因在此?’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逃役筑长城,不堪辛苦,逃匿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妻。’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夫妇礼毕,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并筑城内。超不知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哭,向城号叫。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杞良。即抛骨取之,多是其骨。仲姿不辞归家,乃穿其骨,衣之以衣,裹之以棺,哭而葬之。”唐代首次出现了“仲姿”之名,后世演变为“孟姜女”。
在《同贤记》中,杞良自述为燕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北京产生了关系。在古代燕地虽大,但北京历来为其核心区域。可以推测,孟姜女所居亦为燕地,杞良所筑之长城亦为燕地长城,这就大概和延庆产生勾连。孟家是当地大户,知道秦廷有用钱赎役,或者以家仆代替服役的制度。因此夫妇礼毕,孟超就给杞良定策,让其自往长城工地,然后再派仆人将其替换回来,夫妻即可安稳度日。出人意外的是,杞良刚返回工地,就被主管劳役的官员打死。仆人到工地代替杞良,杞良的尸体已被筑进长城,立刻返回禀告。仲姿得知消息,便到长城工地哭夫,致使长城崩倒,露出的白骨错杂,一时分不出哪些尸骨是杞良的。孟姜女于是挑挑捡捡,把杞良散乱的白骨拼凑成人形,固定之后给尸骨穿上衣服,装进棺材后哭着将其埋葬。
唐代佚名《琱玉集》中的《感应篇》出自《同贤记》,把辨认尸骨的情节进行了细化,使其融入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便将归葬之也。”“滴血认亲”是中国古代的发明,扎根历史将近两千年,孟姜女采用的是“滴骨法”。三国时期,吴国谢承《会稽先贤传》:“(陈)业兄渡海,复见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十六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沥骨上,应时欿血,余皆流去。”由此,“滴骨验亲”之法被奉为圭臬。唐代李延寿《南史》记载,孙法宗之父死于大海,他操刀沿海岸寻找,见到枯骨就用“滴骨法”,十余年后,他体无完肤,仍没有找到。
清代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湖上笠翁曰:余读他传,有谓秦孟姜,富人女也,赘范杞梁,三日,夫赴长城之役,久而不归,为制寒衣。送之至长城,寻问,知夫已故,乃号天顿足,哭声震地,城崩,寻夫骸难认,啮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为夫骸,负之而归,至潼关,筋力已竭,知不能归。乃置骸岩下,坐其傍而死。潼关人重其节义,立像祀之。”可见,在清代时期,“滴血认亲”已经是孟姜女故事的重要情节。延庆地区的孟姜女故事,即沿袭“滴骨法”认亲的情节。
在唐代敦煌石窟发现一首小曲:“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骆山下雪纷飞,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归还。”增加了送寒衣的情节,与《感应篇》虽同为唐代,但情节也有创新。明清时期,孟姜女的故事被进一步加工,有了“燕子送葫芦籽”“葫芦生女”等情节。
元明清时期,孟姜女故事融入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情节则更加丰富多彩。如《理学汇编·文学典》词曲部汇考有曲目《孟姜女》、明代解缙《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戏,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在元杂剧《孟姜女送寒衣》当中,孟姜女哭倒长城后,和想要强娶的秦始皇斗智周旋,十分接近现代人所熟知的情节。其后,从清代至今流传的各种大剧种、小地方戏、电影、话本等,大都以此为蓝本进行创作,“杞梁”谐音为“喜良”,被冠以“范”或“万”姓,但在具体情节上各有特色。因地区不同,民间所塑造的孟姜女形象也不同。北方地区的孟姜女大都悲壮,符合北方人的性格特征。南方地区的孟姜女大都细腻,有时加入奇幻色彩。都融入各地的地方风物,把孟姜女元素附加于山、水、墓、石等,成为地方的特色文化。(未完待续)



打开APP阅读全文